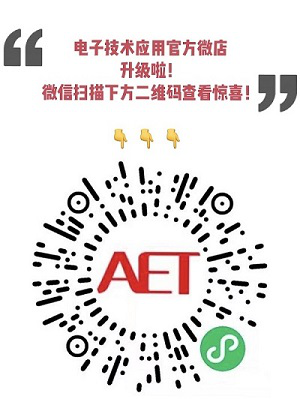歐洲和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以及歐盟委員會和日本政府為應對美中競爭加劇的國際環境而對各自產業政策進行再投資的方式,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去年6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了“半導體和數字產業戰略”,表示半導體在數字革命中的作用,并不像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或工業革命中的蒸汽機那樣,而是“工業中的大米,對所有行業都至關重要和不可替代的”——這個比喻結合了對國家生存的呼喚——每個人都需要大米才能生存,以及日本作為世界上生產最高國際標準大米的國家之一的自豪感。
日本半導體工業的岌岌可危
與歐洲一樣,日本有嚴重的脆弱性,但也有關鍵的優勢。與美國相比,與臺灣韓國的強大制造能力相比,上述關乎生存的提法,反映了日本半導體工業的衰落。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數據,日本在世界半導體市場的份額從1990年的50%,下降到今天的10%。在同樣的三十年里,歐洲半導體的產能份額也經歷了類似的急劇下降,從44%下降到9%。
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既定目標是到2030年保持10%的市場份額。根據政府的戰略文件,這將需要相當大的投資——高達5萬億日元(380億歐元)。這比美國目前正在討論的520億美元政府資金要少,低于歐盟為支持歐洲半導體產業而出臺的政策工具的組合:歐盟將其7500億歐元的復蘇計劃的20%用于數字轉型(盡管其中只有一部分將資助歐洲半導體公司的項目);歐盟還在建立一個公私合營的半導體聯盟,以確保更多的投資,并正在準備第二個關于微電子的歐洲共同利益的重要項目。但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數字只是一個估計,而不是一個批準的預算,日本將調整到與歐洲和美國相當的規模。
經濟產業省對日本半導體衰退背后原因的分析是清晰和直接的,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美國在1986年的貿易談判中強加給日本的:《美日半導體協議》中,日方做出了反傾銷保證,以及在五年內向外國生產商開放日本半導體市場20%的份額條款。
然而,更決定性的是,日本工業在上世紀80年代末錯過了兩次轉型。它沒有投資于邏輯芯片,而是選擇專注于DRAM存儲芯片,而此時美國工業恰恰放棄了存儲而專注于計算能力。結果,日本公司在存儲芯片領域面臨著韓國企業的激烈競爭。而且,就像歐洲一樣,日本錯過了集成電路(IC)設計和IC制造之間橫向分工的列車。這種轉變起源于硅谷和臺灣:加州見證了無晶圓廠巨頭的崛起,博通(Broadcom)、高通(Qualcomm)和英偉達(NVIDIA)憑借為消費設備設計的新處理器,搶占了全球價值鏈的上游;臺積電(TSMC)于1987年創建了代工模式,在不斷創新制造能力的基礎上,耐心地建立了全球領先地位。另一方面,日本沒能保持原有企業的巨頭地位,也沒有創造新的巨頭企業。
日本的供應鏈風險
上世紀80年代末的遺留問題已經難以推翻重來,但日本和歐洲一樣,原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全球價值鏈是根據市場參與者的理性原則組織的,相互依存確保了準入。然而,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嚴重中斷,中美科技戰爭也改變了日本的威脅評估。
目前的短缺已經敲響了警鐘。由于目前的供應短缺,2021年全球汽車行業可能損失高達1100億美元。這影響了日本龐大的汽車業,盡管由于2011年日本東北部地震和海嘯后采取的彈性措施,日本汽車業比歐洲汽車制造商準備得更充分。例如,豐田就完全受益于其芯片儲備政策。如今,從智能手機到服務器和電信硬件,短缺已經擴大到數字經濟中更大范圍的產品。對日本來說,地緣政治競爭,而不是自然災害或全球健康危機,是需要解決的新風險。
這與歐盟強調戰略自主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經濟產業省的出發點是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實力,以及日本抵御地緣政治沖擊的需要。為了滿足這一需求,日本的政策應將其定位為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日本本身應該擁有咽喉要塞,使自己免受敵對勢力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希望在與美國和歐洲的三角相互依存關系中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伙伴。這種堅決的西向展望是一種戰略選擇。
而其他三個亞洲半導體參與者也是日本選擇這種戰略的部分原因:臺灣是重要的合作伙伴,韓國主要是作為存儲芯片領域的競爭者,而中國的競爭力越來越大。
具有一定諷刺意味的是,經過歷史的曲折,中國故意傾銷導致日本半導體行業部分破產的風險,如今已被日本認真考慮,而35年前,日本正是因為半導體傾銷行為受到美國的貿易制裁。時代完全變了,在半導體產業極度依賴進口的情況下,中國制定了全球領導的愿景。隨著中國不可避免地迎頭趕上,一旦在半導體行業突破某些瓶頸,中國將獲得巨大的戰略影響力。日本在2010年成功地阻止了中國稀土出口的斷供威脅,但半導體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害。
這種風險評估導致了一個在歐洲也聽到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最重要的是擁有扼制點和培養優勢。顧名思義,日本的集成器件制造商(IDMs,即設計和生產半導體的公司),就像歐洲的公司一樣,并不以掌握半導體制造的尖端節點為目標。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的半導體分公司的故事,與歐洲三大IDM公司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英飛凌(Infineon)和恩智浦(NXP)的故事相似。沒有臺積電,并不意味著它們的業務沒有蓬勃發展,它們在微控制器、傳感器和功率半導體方面仍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日本經濟產業省建議投資于研發和資本支出,以保持日本在功率半導體和傳感器領域的高度競爭力。對于用于汽車工業和智能工廠的微控制器,日本經濟產業省呼吁供應鏈多樣化,以保持日本的高市場份額。日本在許多半導體材料領域擁有50%的市場份額,這是一張強有力的牌。2019年,當它對出口到韓國的光刻膠實施限制時,表明已經準備好打這張牌。
日本和歐洲對先進晶圓代工廠的討論
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戰略文件強調了先進邏輯半導體在國內生產的重要性,歐洲的觀察家們對這個問題非常熟悉:自去年以來,對于是否要在歐洲建立一個跨越7納米制造工藝門檻的先進晶圓代工廠,持肯定和否定意見的人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歐洲最先進的晶圓廠,在德累斯頓,使用22納米的工藝技術。日本最先進的晶圓代工工藝是40納米。很快,最前沿的將是2納米——臺灣剛剛批準了臺積電在新竹的新工廠建設。由于最先進的邏輯處理器的市場基本上是最先進的消費數字設備,如iPhone,歐洲的許多工業企業認為,補貼先進的晶圓廠將是在浪費公共資金。他們的觀點被Global Foundries在德累斯頓的最先進晶圓廠的負責人很好地捕捉到了,他說:“我們相信,從55納米到22/12納米的德累斯頓技術區間,將為歐洲工業在2035年后所需的90%的芯片提供解決方案。我們已經準備好或正在開發未來15年所需的解決方案”。
這個問題有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是在需求激增或海外供應中斷時,為歐洲和日本汽車及其他創新半導體工業消費者保持穩定的供給,因此,不需要跨越7納米的門檻,但有更先進的本地晶圓廠將緩解設計者的壓力,因為他們為自己的產品尋求更高的性能。
另外一方面則是要考慮二十年后的產業格局會是什么樣子。從這個角度來看,先進制造業的問題是不能被忽略的。5年后,使用7納米及以下工藝的邏輯芯片將集中在韓國、美國和臺灣。由于技術轉讓的限制,中國仍將面臨技術瓶頸,但它將盡其所能克服這些障礙。在日本和歐洲,將會有更多的IC設計公司需要先進的工藝制造。
它們可以從臺積電購買芯片,包括可能從其位于亞利桑那州新的5納米芯片廠購買。三星和英特爾也可能提供選擇。但生產中斷的風險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全球需求可能超過晶圓廠產能的情況下。
這讓歐洲和日本面臨同樣的困境:它們是否應該專注于現有的優勢并擁有關鍵點?它們是否應該優先支持尖端集成電路設計者的出現,以便在本土創造對先進制造工藝的需求?即使日本和歐洲市場目前規模太小,無法消化產能,它們是否應該在假定此類產品存在全球市場的情況下,補貼臺積電或英特爾建造先進晶圓廠?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歐洲和日本未來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地位。它們都打算加大對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生態系統的研發和創新支持。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文件強調了“超越摩爾”的研究,目標是創造出在單一芯片中結合邏輯、內存和傳感器功能的電路。摩爾定律指出,集成電路中晶體管的數量大約每兩年翻一番,并根據經驗描述和預測了工業流程的微型化。但是2納米(一塊芯片上兩個晶體管之間的距離)可能是該定律的物理極限,而新的前沿領域是在一塊芯片上的垂直整合層。長期以來,超越摩爾也一直是歐洲企業和研究中心的優先事項。
但歐盟和日本目前在處理這一問題上有一個關鍵的區別。日本已經確定了與臺積電建立長期關系的方向,起步階段規模相對較小;而歐盟正在考慮各種選擇,在撥付公共資金時,仍可能優先考慮先進的邏輯集成電路設計,而非制造。
今年早些時候,臺積電宣布在東京附近的筑波投資一個受補貼的研發中心,該設施匯集了約20家日本公司和日本領先的研發公共機構——日本先進產業科學與技術研究所(AIST),致力于先進制造業的垂直整合。現在看來,臺積電在日本建造首個晶圓代工廠的計劃幾乎暢通無阻,臺積電董事長Mark Liu證實,該公司目前正處于“在日本建立一家專業技術工廠的盡職調查過程”。日經亞洲最近報道稱,該工廠將于2023年投入運營,主要使用28納米技術為索尼生產圖像傳感器。這不是先進的邏輯芯片,但這是與臺積電重建日本半導體生態系統的又一步。
臺積電與日本的談判,比與德國的“非常早期階段”更為深入,臺積電最終可能會在德累斯頓投資,以回應德國工業的需求。但日本的做法表明,支持一個行業的現有優勢,并不一定排除對大型工業項目的追求。